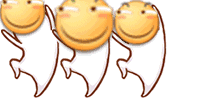天已亮。她躺在病床上,身上被贴了电极片,胳膊上被扎了吊瓶针,鼻子上被吸上了氧气。趴在床边的是她大女儿,可能熬了一夜,现在睡着了。
我还记得午夜时分她被送过来时的场景,一大家子人急促的脚步声将我惊醒,然后推车慌张地来到八号病床的前面,她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小儿子在护士地指导下,慌乱又小心地将她放床上。接着护士给她安上心电监护和氧气瓶,测血压,量体温……
现在医生也来了一大群,其中一个还是外国友人,他们和那个外国友人叽里呱啦的谈话、讨论。
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,觉得这几天发生的事似是演戏——大前天中午她还在家里的旧沙发床上,和她刚一周岁的大孙子玩耍,早上六点起来给猪圈里的猪撒了饲料,甚至走到村子旁边的菜园给她种的菜锄了锄草。结果下午忽然失去意识,被她大儿媳妇送到县里的医院;前天她就在输水,她抬头看着输液瓶里的药水,忽然觉得,真像人生啊,滴着滴着,一个分神就没了;昨天下午县医院的医生们商量了商量,自知水平不够,便让家属连夜转院……
医生们似是讨论完了,其中带头的和她的一众家属解释,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以老人目前的状态,只有做开颅手术是最好的选择,而且情况紧急,要现在就做。家属们连连点头,表示只要能救我们老太太,你们怎么样都成。
于是这个九月清晨,老太太被她二闺女拿着手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了字,随后她换上手术服,被医务人员抱上推车,推进麻醉室,还有手术室。
下午,我将采集的我妈的尿常规样本,送去二楼的采集室,并看到了她的家属们,我看到二儿子的手被包着,他面前的瓷砖墙上,呈裂痕,还有一摊红色。
再晚些时候,我已回病房,她的大儿媳妇、小儿子,大闺女进病房急匆匆地收拾东西,眼角都挂着泪水,其中一个还在低声啜泣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分——割——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这篇九月清晨,在今天早上——一个七月清晨里写完,灵感源自前几天我妈隔壁病床的老太太。妈妈二十多天前因脑出血住院,半月前转至河南省人民医院,万幸现已无大碍。这期间八号床病人换了四个,文章中说的是第一个,那个老太太来自兰考,叫李秀兰,因开颅手术失败,已不在人世。她在病床上时,精神很好,护士来换药问家人她叫什么,她总是积极地抢答,因此,我记着了她的名字。也想,写一写这质朴平凡的老人,生命里的最后时光。好长时间未曾起笔,过了长吁短叹的年纪,写的不好欢迎指正,但别讽刺得太猛。

- home
首页
-
view_list分类keyboard_arrow_down
-
access_time归档keyboard_arrow_down
-
view_carousel页面keyboard_arrow_down
rss_feed
RSS订阅